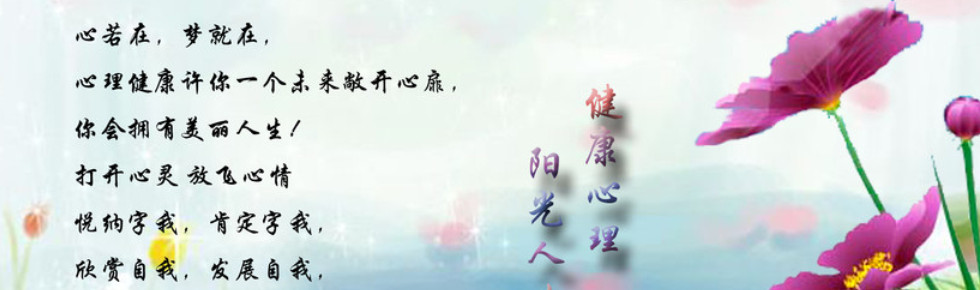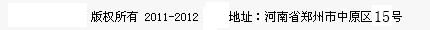年,我们过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春节:
我们一边被春晚小品逗笑,一边被朋友圈里的新闻泪目;我们认为外面的世界十分危险,而我们的父母认为我们小题大做;我们很想喝酒搓麻踏破别人家门槛,却选择做个不给国家添乱的死宅。虽然中国已经不是非典时的中国,我们有了更先进的医疗技术、更高效的物流体系、更强大的政治地位,但当我们再一次面对疫情,某些地方机构在大众舆论面前,依然像个没毕业的小学生。
我想讨论一下,在这次疫情发生期间,上到政府下到每个市民,正在面对的几个传播学问题:
我们都知道「堵不如疏」,为什么某些机构还是企图「控制」舆论?我们都喊「不信谣不传谣」,为什么一到疫情还是谣言四起?很多人都说“就差以死相逼了”,为什么就是「说服」不了父母戴口罩?非典在前,而新型肺炎的教训正在发生,如何让人们「长点记性」?
01政府/机构,可以「控制」舆论吗?
12月8日,武汉出现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;1月2日,央视报道武汉《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》;1月19日,武汉市疾病防御控制中心主任李刚称:疫情可防可控;1月21日,湖北省省委书记、省长等领导一同出席了春节团拜会的文艺演出;1月23日,湖北省长王晓东接受采访,称武汉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;1月24日,湖北省才尾随各省政府,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。……
从武汉和湖北省的舆论操作方法可以看出来,他们一直在试图「控制」舆论。但无论是非典期间,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型肺炎,以及无数个舆论事件都告诉我们:舆论是无法控制的。
既然大家都知道「堵不如疏」的道理,为什么还是心存侥幸地想堵一下呢?
因为堵不对,但是疏也是有bug的。
舆论是个放大器,它可以把好事和坏事,都千百倍地放大。在舆论监督面前,疫情危险可以被放大,恐慌情绪可以被放大,官员失职可以被放大!而没有人喜欢放大自己的错误……
于是,在失控的舆论面前,掩饰终于变成了失信,小错误终于酿成了大败局。
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一点:我们要求官方机构公开透明,时时接受舆论监督是合法合理的,但在实际执行中,这个方法是违背人性的、是极难落地的。
既然控制舆论不对,不控制舆论又极难落地,政府/机构到底要怎么做?
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传播学的理论——议题设置理论(theagenda-settingtheory)。
伯纳德·科恩对“议程设置”给过一个有影响力的表述,他说:“在多数时间,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,可能并不成功;但在告诉读者该想些什么时,却是惊人地成功”。
这个理论告诉我们:通过设置社会议题,政府/机构虽然不能控制大众说什么,但是可以「引导」大众讨论什么。
做舆论传播,就好比和大众坐在一个大厅里开会,如果你强硬地命令参会人员不准玩手机、不准小声嘀咕、不准走神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你可以通过设置会议议题,发动参会人员一起讨论一个又一个话题,从而间接地影响参与人员。
人都喜欢表达自我,而不是封闭自我。所以,议题设置理论是一个更符合人性的舆论管理方法。政府/机构要做的就是:既要对大众公开事实,同时要规划大众